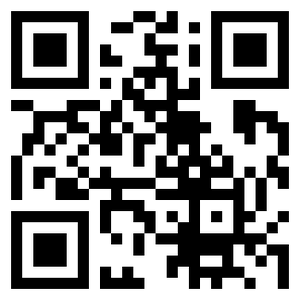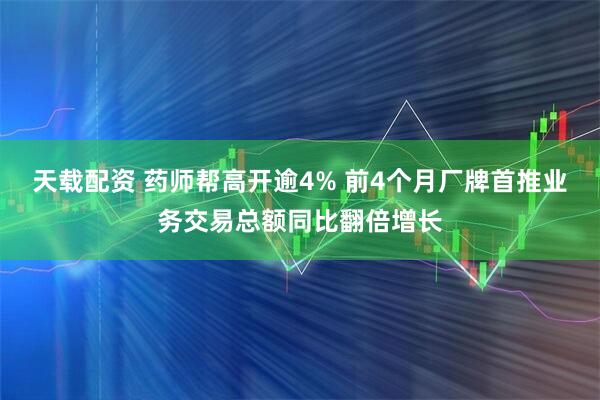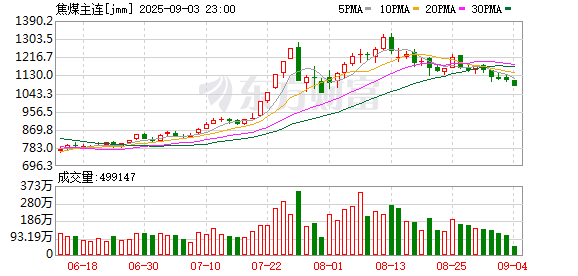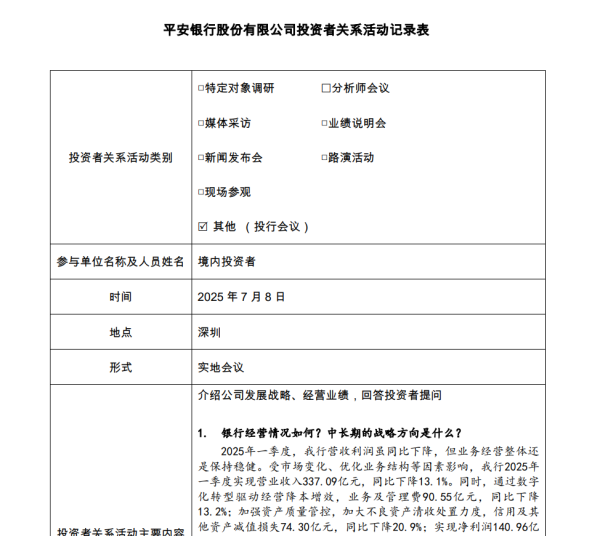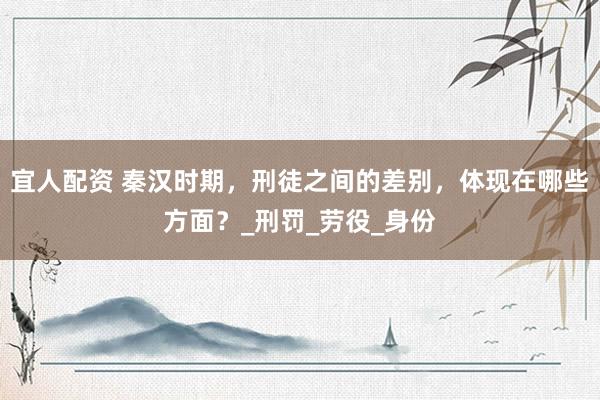
引言宜人配资
秦汉时期,刑徒之间的差别,体现在哪些方面?《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载: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舂,满三岁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妾。隶臣妾一岁,免为庶人。隶臣妾满二岁,为司寇。
司寇一岁,及作如司寇二岁,皆免为庶人。由此可知,“城旦春”“鬼薪白粲”“隶臣妾”“司寇”等劳役刑名,其等级由重至轻的顺序依次为城旦舂一鬼薪白粲一隶臣妾一司寇。
既往研究从传世文献的史料记载来看,一般认为秦汉时期的劳役刑是根据罪的轻重来设定相应刑期的。但20世纪80年代以降,作为当时史料的简牍资料陆续公布。
据此提出了秦及汉初的刑罚未设定刑期,自西汉文帝刑制改革始设定刑期的观点。
展开剩余94%一、刑徒的可视性差别
关于刑期之有无至今仍存争论,但除却部分有期的劳动处罚,当时的刑罚不存在刑期,这在日本学界是较为权威的观点,本文亦从之。
在这些讨论中,如何理解未设定刑期也成了一个问题。若没有刑期,则在当时一旦成为刑徒,基本上就要承担终身劳役的义务。
然而,根据资料可确认,部分刑徒未被强制劳动,存在无法劳动的未成年刑徒,且子女将继承刑徒身份,故产生了当时的刑罚是否以劳役为第一要义的疑问。
而为了全面地理解此种情况,有学者提出,在秦及继之的汉初刑制中,劳役刑是否亦可谓以身份贬降为第一要义的“身份刑”。
这样,刑徒被认为是比一般民众更低的身份,被排除在一般民众形成的秩序之外。
如此,时人将贬降了身份的刑徒视作被蔑视及排除的对象,若将此作为刑罚的效果,则为使身份遭贬降的刑徒一望而知,刑徒的身份差异应是可视化的。
区分刑徒与一般民众,最显著的特征即身体刑之有无。身体刑作为损毁肉体的刑罚,与劳役刑配合使用。
对所犯罪行较轻的司寇、隶臣妾,以及拥有特权身份的鬼薪白粲,施以称作“耐”的身体刑;对罪行最重的城旦舂,则施以不可能恢复的、损坏肉体的“肉刑”。
以肉刑为首的身体刑,可理解为其将犯罪者异形化,进而实现将犯罪者排除出社会或共同体的目的。
这样的身体刑将刑徒与一般民众相区别,若当时的刑罚应称作身份刑,则根据被判处的刑罚之轻重,在刑徒之间也应设定了身份的上下层级。
这样一来,从秦代的资料来看,除身体刑之外刑徒也存在外表可见的差异,这点应是可以确认的。
如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司空律》简147载:城旦舂衣赤衣,冒赤氈,枸椟標秋之。
如此可知,城旦舂被强加了穿戴红色囚徒服、红色帽子和刑具的义务。过去学界认为,秦的刑徒应是全都穿着“赭衣(红色囚徒服)”。
然而,《司空律》简134—135的记载如下:鬼薪白粲,群下吏毋耐者,人奴妾居赎赀责(债)于城旦,皆赤其衣,枸椟摞枚,将司之。
类似的还有《司空律》简141:隶臣妾、城旦舂之司寇居赀赎责(债),齩(系)城旦舂者,勿责衣食。其与城旦舂作者,衣食之如城旦舂。
律文规定,城旦舂之外的刑徒、奴隶,在与城旦舂服同样劳役的情况下,穿着与城旦舂同样的衣服。
这表明,城旦春之外的刑徒原本穿着的是与城旦舂不同的衣服,法律设定了刑徒之间的服装差异。
附带说明一下宜人配资,与《司空律》简147同样的规定,亦见于《岳麓秦简(肆)》简167-168,可见对刑徒服装的规定有秦一代几乎是一以贯之的。
此外,《岳麓秦简(肆)》简167-168载:司空律曰:城旦舂衣赤衣,冒赤氈,构椟秋之。诸当衣赤衣者,其衣物毋小大及表里尽赤之。
虽然律文中规定“当衣赤衣者(必须穿着红色衣服的人)”,但亦可据此推测出刑徒中存在不是必须穿着红色囚服人。
最初,红色囚服被认为源于上古的象刑(不科处肉体刑罚的表象性刑罚)。
如《太平御览》卷六百四十五所引《尚书大传》载: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纯,中刑杂履,下刑墨蠓,以居州里,而民耻之。
如其所述,根据刑罚之轻重有差异地设计刑徒的服装,红色囚徒服是“上刑”,即适用于最重的刑罚。
在秦代,较死刑次之的重刑即对城旦春附加穿着红色囚徒服的义务,可以认为是继承了这一做法。
尽管学者们认为,秦代刑徒的服装是城旦舂与除其以外的其他刑徒的区别所在,但其他刑徒具体穿着何种服装,尚未明确。
在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金布律》简94-95中可见这样的规定,即对于没有妻子的隶臣,及由于年老或年幼而无法自行负担衣服的隶臣妾,官府为其支付衣服的费用。
这表明隶臣妾原本是自行负担衣服费用的,且从这一点可推测与隶臣妾服装相关的制约似乎并不那么严格。
综上所述,一方面,秦代一般民众与刑徒首先依据身体刑之有无而差别化,刑徒之间的身份高低则根据身体刑的程度与服装的差异来表现。
另一方面,如前引《司空律》所述,城旦舂以外的刑徒在与城旦舂共同服劳役的情况下,被附加了穿着与城旦舂相同衣服的义务。
这可能是出于方便的考虑,即根据每种劳役内容统一管理刑徒。可以说,原本用以表现刑徒之间身份差异的衣服也成为区分劳动力的标志。
陶安指出,在睡虎地秦简的时间点刑制已经产生了变化,从对刑徒服装的规定也能看出这一点。关于汉初刑徒的服装。
可见《汉书》卷九十七《外戚传》:吕后为皇太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钳衣赭衣,令舂。因吕后而沦落为舂的戚夫人穿着赭衣、佩戴钳。
由此可知,在汉初,城旦舂亦被强制穿戴红色囚徒服和刑具。但在《二年律令》中未见直接规定刑徒服装的律文,《二年律令金布律》简418-420仅可见为刑徒分发衣服的规定。
诸内作县官及徒隶,大男,冬稟布袍表里七丈、络絮四斤,绔(袴)二丈、絮二斤。大女及使小男,冬袍五丈六尺、絮三斤,绔(袴)丈八尺、絮二斤。
未使小男及使小女,冬袍二丈八尺、絮一斤半斤。未使小女,冬袍二丈、絮一斤。夏皆稟禅,各半其丈数而勿稟绔(袴)。布皆八稷、七稷。以裘皮绔(袴)当袍绔(袴)可。
关于此处“徒隶”一词,目前存在不同解释,但从里耶秦简的记载来看,已可明确“徒隶”中包含了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故“徒隶”有可能指代刑徒的整体。
若是如此,则在相关条文中,自隶臣妾至城旦舂的汉代刑徒的衣服一律统一管理,这一点引人注目。这种刑徒衣服的统一化,与秦代强调刑徒间身份差异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
此外,在《二年律令具律》简88-89对女性减刑的规定中,规定了女性的耐刑减为“赎耐”,由此可知,可通过纳人金钱以回避作为身体刑的耐刑。
这表明汉初的身体刑已不再是区分刑徒与一般民众的绝对身份标志,而有了可替代的身份标志。可以推测,或许统一的刑徒衣服就是这种身份标志。
《汉书》卷五十一《贾山传》所载,为西汉文帝初年之事:赦罪人,怜其衣赭书其背,父子兄弟相见也而赐之衣。宫宅潔认为,在刑徒的赭衣上书写特殊文字成为辨别刑徒的标志。
与秦代不同,汉初的刑徒在按照统一的红色囚徒服区别于一般民众的基础上,再以衣服上书写的文字或记号,按等级进行分类和管理。
在睡虎地秦简时期,为了便于管理,已经开始统一刑徒的衣服了,并在汉初得以定型,据此可知,刑徒之间应该已经存在身份性差异,也就是说身份刑的要素正在被逐渐淡化。
二、文献的记载
如前所述,虽然秦及汉初的刑罚是无期刑,身份遭受贬降便是终身,但在某种条件下也存在恢复身份的可能性。
据传世文献史料的记载,亦可确认数个因“赦(恩赦)”及褒赏等而摆脱刑徒身份的事例。且在睡虎地秦简中,亦可见允许隶臣妾以返还爵位或代替劳役来恢复身份的条文。
这表明刑徒身份的恢复不仅是特例性的措施,也是依据法律的恒常性保障。但睡虎地秦简所见的赎身规定仅针对隶臣妾,这一点在先行研究中已特别强调。
与隶臣妾能够赎身相对比,城旦舂和鬼薪白粲并未被赋予提升身份的机会,可理解为他们是一种被完全排除在身份秩序之外的存在。石冈浩将此原因主要归结为“收”之有无。
“收”是一种没收犯罪者的妻子和财产的制度,适用于城旦、鬼薪以上的男性犯罪者。
石冈浩认为,对于不适用收的隶臣,可以保有其家庭,以家庭归还爵位或替代劳役的方式来恢复身份;而对于适用收的城旦、鬼薪则不存在这种可能。
因收而导致的家庭解体才真正剥夺了他们恢复身份的机会。然而,在睡虎地秦简之后公布的汉初《二年律令》中,不仅对于隶臣妾,还可见释放城旦舂、鬼薪白粲的规定。
如《二年律令钱律》简204-205:捕盗铸钱及佐者死罪一人,予爵一级。其欲以免除罪人者,许之。捕一人,免除死罪一人,若城旦舂、鬼薪白叛二人。
隶妾、收人、司空三人以为庶人。盗铸钱,即伪造货币。可以看出,捕获实施此行为的犯罪者。
不仅是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甚至犯死罪者,也能获释。但如何综合理解这一钱律的规定与睡虎地秦简中的赎身规定,则成为一个新的问题。
对此,石冈浩得出的结论是,钱律的规定说到底只是针对盗铸钱这一严重犯罪的特殊措施。
有可能恢复身份的人群也仅限于隶臣妾。但是,既然同时论及时代相异的睡虎地秦简与二年律令的规定,我们可以将其中一者视作特殊措施而排除于考察对象之外吗?
正相反,特例性规定所表现出的刑制上的变化才应予以注意。着眼于自秦至汉初变化的研究,我们可举出陶安的成果。
对此问题,陶安推测,在秦末乱世中,因大赦和功勋而致使免罪的范围持续不断地扩大,并就此为汉初所沿袭,故《二年律令钱律》中可见广泛的免罪权。
秦末以降的赦令频发是刑制变化的背景,提出这一观点的成果有很多,对此宫宅潔也有详细的研究。
然而,仅从《史记》卷六《始皇本纪》所见“久者不赦(很长时间不施行赦)”的记载来看,可以认为在秦王政、始皇帝时期并未施行赦,但因《岳麓秦简》的公布。
可知秦王政时期亦施行过赦。例如,在案例“猩、敞知盗分赃案”中,就有秦王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年)的记载:敞当耐鬼薪,猩黥城旦。遝戊午赦,为庶人。
如此,城旦和鬼薪因赦而获得了释放。陶安指出,岳麓秦简的公布,可列举出秦王政时期至少发布了两次赦令,故其是重新审视基于汉代文献所得通说的珍贵材料。
既然存在传世文献史料并未记载的赦令,则或许秦代赦令的施行比以往设想中更加频繁。而且这意味着,从秦末至汉初兴起的刑制上的变化不能仅从赦令的频繁颁布这一因素来推导。
话说回来,钱律的规定可以解释为免罪权的扩大吗?再次确认后可知,《二年律令》所见的赎身规定仅此钱律一条。
该条文亦可被列举为显示爵的赎身功能的条文,但说到底其仍是为阻止盗铸钱这一重大犯罪,而在将被赐予的爵位返还之时所得的恩典。
也就是说,这并不能理解为普遍意义上的允许通过返还爵位来为刑徒赎身。且睡虎地秦简中所见的隶臣妾的赎身规定,在《二年律令》中已不可见,这一点才应引起注意。
而这也意味着,在汉初,与睡虎地秦简时期的情况有所不同,刑徒及其家属主动的赎身是不被允许的,只有以国家的恩赦或奖赏等这类国家主导的形式方可恢复身份。
在秦代,赎身是仅隶臣妾可被许可的特权,到了汉代则取消了这种特权,城旦舂以下的刑徒变为由国家统一管理,可以看出国家意志在刑徒恢复身份中发挥了更加强烈的作用。
这或许表明国家能够更加高效地、任意地管理刑徒了。如上所述,从恢复刑徒身份的角度亦可看出,从秦到汉初,国家对刑徒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并且我们可以认为,这种变化与身份刑要素的消失具有同样的趋势。
三、刑徒的“家庭”
最后,笔者也想探讨与刑徒“家庭”相关的问题。如前所述,既往研究认为,“收”造成了刑徒之间的等级差别,不施行“收”的隶臣能够保有家庭,与之相对的是城旦、鬼薪则无法保有。
为了印证这一点,可参看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司空律》简141-142:隶臣有妻、妻更,及有外妻者,责衣。
由此可知,隶臣可拥有妻、妻更及外妻等女性配偶一此外,还可见《金布律》简94-95:稟衣者,隶臣、隶府之毋(无)妻者及城旦,冬人百一十钱,夏五十五钱。
由此可知,与城旦有所不同,对隶臣假定的是其有妻子的情形。故可据此理解为,一直以来,隶臣是可能成家的,但城旦则不可能。
然而,在近年公布的《岳麓秦简(肆)》简266中可见:黔首为隶臣、城旦、城旦司寇、鬼新(薪)妻而内作者,皆勿稟食。这表明不只隶臣,城旦、鬼薪也有可能娶妻。
“黔首”是始皇统一后用以改称“民”的词语,其中不包含奴婢或刑徒,指代的是自由身份之人。
也就是说,至少在始皇时期以降,因“收”而被没收了妻子的城旦和鬼薪,也可能重新与自由身份的女性结婚。
一直以来的理解是,刑徒被附加了在刑徒专门的居住区生活的义务,尤其是城旦舂被限制与一般民众的接触。
基于此种理解,并假设一般民众与刑徒能够缔结婚姻关系,可举出居赀赎债(以劳动来偿还赀刑、赎刑等财产刑或欠官府的债务)的例子。
一般民众因居赀赎债而与刑徒共同服劳役,即使缔结婚姻关系也不会不自然。但另一方面,本条简文亦可理解为一般民众因成了刑徒之妻而被科征劳役。
而根据不对刑徒之妻发放粮食的规定,可知国家或许并不提倡这类一般民众与刑徒之间的婚姻。并且按照后一种理解,城旦舂等刑徒在内作的场所之外是可能与一般民众交流的。
故其接受的应是比既往认识中更加宽松的隔离和管理。
尽管关于城旦与鬼薪家庭的规定仅此一条,详情未明,但城旦和鬼薪也能够组建家庭这一事实。
就已经表明了我们似有必要重新检讨既往研究所指出的隶臣妾与城旦舂、鬼薪白粲之间存在绝对的等级差异这一观点。
结语
至于汉初宜人配资,因与刑徒相关的史料很少,其家庭所处的情况并不清楚。唯一可见的是《二年律令户律》简307中或与刑徒之“家”有关联的规定,但对其应如何理解仍是一个问题。
发布于:天津市久联优配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